“伙計,我知道你有聽覺問題……因為剛剛我問了你三次問題,你才回答我。”今年1月,安迪·格魯夫在可能是其人生最后一次聚餐中,對與他共事了25年的老友——斯坦福商學院教授羅伯特A.伯格爾曼(RobertA.Burgelman,下稱“伯格爾曼”)說。
“我知道你不想檢查。但是你必須要檢查,否則兩年后你會后悔。”安迪·格魯夫隨后又說道,臉上瞬間閃過在伯格爾曼看來“有些諷刺卻總是代表友好”的微笑。
這位硅谷傳奇人物,一代硅谷人心中的“燈塔”,在不久后的2016年3月21日,心臟停止了跳動。
安迪·格魯夫的一生中,早年逃亡、中年帶領英特爾壯大和渡過難關、晚年教書培養學徒兼和病魔斗爭。直到生命最后那段時間,他都始終保持著自己鮮明的個性,即使是告誡相識多年的好友要注意身體,也不肯用更溫和、委婉的方式和語氣。了解他的人會知道,這就是安迪·格魯夫,性格上的棱角無法抹滅他推動PC時代崛起、留下諸多經典管理思想的光芒。
“安迪一次又一次地讓不可能成為可能,他激勵著一輩又一輩的科技人、制造者和商業領導者們不斷前進。”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布萊恩·科再奇說。
就連英特爾在移動領域最大的競爭對手、高通公司創始董事長兼名譽首席執行官艾文·雅各布也說出:“計算機、無線/智能設備都從安迪·格魯夫的貢獻中獲益,我們應該向他深深致謝。”
嚴厲老板
“在我看來,英特爾這家公司的味道,其實就是安迪·格魯夫的味道。”英特爾中國區員工徐鵬(化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當你走到楊旭(英特爾全球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的‘格子間’,根本看不出來他的工位和其他員工有任何區別,“我剛進入英特爾時,對這一點感到特別震撼。我們每個會議室都一定會掛一塊表,這種慣例源自安迪·格魯夫討厭冗長的會議。”
早期的硅谷,科技公司經理都有自己的辦公室,不過當創業公司漸漸發展壯大后,這種特權文化一定程度上容易滋生公司內部糾葛。安迪·格魯夫在當時提出,無論英特爾公司總裁、經理還是員工,都必須坐在完全一樣的格子間。后來,“格子間文化”通過英特爾傳遞到硅谷以及更多的地區和公司。
安迪·格魯夫一生有三本重要著作:《游向彼岸》、《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高產出管理》(又名《格魯夫給經理人的第一課》)。《游向彼岸》是對安迪20歲以前人生的總結,他的逃亡經歷;《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集中了硅谷工程師文化精髓,“偏執”(國外理解為執著到近于病態)至今仍是不少產品經理人的人生格言;《高產出管理》,則是安迪帶領英特爾科技創業公司成為全球科技巨人的管理經驗濃縮。
“當初創公司部門壯大后,會議變得冗長,安迪·格魯夫就提出來我們要‘高效會議’,從那個時候起,硅谷就有‘高效會議’的說法,有人是專門做會議記錄的、有人是管時間的、有人是管會議流程的。英特爾的這種管理方法在當時并不多見。”徐鵬說,如果覺得跟自己沒關系,那就有自由可以不參加各種會議,這也是安迪·格魯夫‘高效會議’思想中特別旗幟鮮明的一點。
1968年,當戈登·摩爾、羅伯特·諾伊斯和安迪·格魯夫離開仙童創立英特爾時,戈登·摩爾和羅伯特·諾伊斯忙于技術和外交,而安迪·格魯夫則負責英特爾公司具體管理和經營。
“安迪·格魯夫是這種不屈的人,特別執著、有沖勁、不服輸、一定要贏……充滿了這樣的精神。我覺得英特爾這么些年經歷了很多大的坎坷,一直到今天還能穩穩當當地往前走,是因為有這個拼搏的基因在。”徐鵬認為。
早先的時候,當摩爾回憶起英特爾早期創業時光,覺得那段時間特別美好,因為他每天都專注于技術,而在英特爾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資金、人員流動、具體業務問題,都是安迪·格魯夫在解決。
“他具備科學家的分析方法,同時又能通過坦誠而深入的對話去吸引他人,在個人電腦、互聯網和硅谷崛起的時代,支撐了英特爾的成功。”英特爾現任董事長安迪·布萊恩這樣評價作為前CEO兼董事長的安迪·格魯夫。
戈登·摩爾、羅伯特·諾伊斯、安迪·格魯夫,共同構成了英特爾三角支架的堅實底座,而安迪·格魯夫對公司管理中實際問題的敏感和準確把握,是英特爾能夠迅速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
“WhatAndygives,Billtakesaway。”安迪·格魯夫掌控英特爾時,硅谷就流傳著這句話,意思是無論安迪提供多高的硬件性能,微軟CEO比爾·蓋茨都會把它消耗掉,消費者為了獲得更好的體驗也就不得不繼續更換新電腦。安迪·格魯夫和比爾·蓋茨兩人聯手,英特爾和微軟形成的芯片加操作系統(硬件加軟件)聯盟,至今仍是PC行業無法翻越的高山。
“安迪·格魯夫是老一代硅谷人的象征,這里的硅谷指的是硬件、IT產品的意思。安迪·格魯夫講的‘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是在技術上、在硬件突破上的‘偏執’,所以才有了“摩爾定律”。說起來很簡單,但18個月翻一番,這后面都是工程人員的心血。”海銀資本合伙人、美國科技創新觀察家王煜全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刻薄”教授
“1988年8月,我收到一封來自校長辦公室的郵件,信中寫安迪對商學院職位感興趣,那個時候,他才55歲,可以說是依舊處在黃金年齡,而且擔任英特爾的CEO。不過,安迪顯然決定急流勇退。”伯格爾曼說,“他燈塔般的智慧和非凡的個性,一直留在我心中。”
直接、刻薄、簡短、一對一方式,是伯格爾曼對教學和生活中安迪·格魯夫印象的濃縮,或者按照伯格爾曼的理解,安迪·格魯夫在“不斷探索事實真相,同時用清晰簡單詞匯表達令人難忘的觀點”。
按照王煜全的理解,安迪·格魯夫的“偏執”沒有中文含意中“憤世嫉俗”、“反文化”這一層意思,更多是對于技術和工程“執著到病態”的一種堅持,“其實很家庭、很本分,安迪·格魯夫是這一類的代表。”
他曾直言不諱地向伯格爾曼指出,“你對你自己和對我都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你的問題在于,你對你學生的要求卻不夠嚴格。”他甚至會讓他的妻子、丈母娘來斯坦福商學院聽他講課,幫助改進講課方式。
這種一旦決定了要做一件事,就全心投入、一往無前的風格,也曾讓安迪·格魯夫在英特爾的下屬活得戰戰兢兢,他們總是擔心自己因為犯錯而被開除。“你越成功,就有越多的人想搶走你的一部分生意,再搶走一部分,直到你一無所有。”安迪·格魯夫在自己的著作《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中有這么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
“他有一種天分,能夠給員工從未遇到過的嚴厲鞭策,并讓員工愿意取悅他,”哈佛商學院教授DavidYoffie,戴維·約菲這樣評價安迪,“他是一個很難取悅的人。”
伯格爾曼回憶文章中提到一個故事。有一次,安迪·格魯夫丈母娘來斯坦福商學院聽課,安迪很生氣,“因為他認為他丈母娘沒有好好聽課,而只是在走神,”伯格爾曼說,“這非常有趣,因為安迪不僅對自己要求嚴格,也對他身邊的人有同樣嚴格的要求。”
硅谷傳奇人物史蒂夫·喬布斯曾在事業迷茫時,給安迪·格魯夫打了一個電話,征詢安迪對自己是否應回歸蘋果公司的看法。“我給他列舉了回歸的好處和壞處,說到一半時他打斷我說:‘史蒂夫,我才不在乎蘋果會怎么樣。’我愣住了,但就是在那個時刻,我認識到我是在乎蘋果的——我創建了它,它的存在對世界是件好事,我決定暫時回去幫他們招聘CEO。”
即使如此,更多與安迪·格魯夫接觸時間較長的同事、朋友,了解他擅長通過“諷刺”洞穿本質,讓其他人因此而印象深刻,也理解了他的“偏執”并無惡意,而是從言論上由內而外在傳遞他的價值觀、對事物的灼見,從行為上對自己和周圍人一致的嚴格要求。
硅谷“燈塔”
安迪·格魯夫身上的“不屈”和“危機意識”,和他早年的經歷不無關系。自傳《游向彼岸》中記載了他早年的逃亡生活。
1936年9月2日,安迪·格魯夫出生于匈牙利,安迪的父親二戰期間被征到猶太人勞工營,而他和母親輾轉于匈牙利各地躲避拘捕,他的母親會堅持每天清晨五點鐘督促只有幾歲的安迪起床學習英語,為某天可能到來的逃亡進行準備。二戰后,1956年匈牙利起義遭蘇聯鎮壓,安迪徒步從匈牙利逃到奧地利,隨后逃往美國。
20世紀60年代初,安迪·格魯夫抵達硅谷,在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學位后,進入仙童半導體成為戈登·摩爾的助理。1968年,他和羅伯特·諾伊斯、戈登·摩爾一起創立了英特爾。
“摩爾定律”后來成為半導體技術規律中的經典,安迪·格魯夫管理思想也成為硅谷、全球管理思想中的經典。半導體集成度歷年不斷提高,背后的工程師文化要求精益求精,二者在技術、管理不同領域提煉源于半導體行業的經驗。
英特爾發展過程中,日本半導體業一度對主要開展存儲芯片業務的英特爾形成生死存亡壓力。安迪·格魯夫最終做出明智決定:在他的領導下,英特爾將業務核心從存儲芯片全面轉為CPU計算芯片,帶領英特爾走過了存儲芯片的“死亡之谷”。
“在這段時間里,英特爾公司生產出了386和奔騰等處理器,公司收入從19億美元躍升至260億美元,也給PC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英特爾公司這樣介紹安迪·格魯夫的貢獻。
事實上,通過聯合比爾·蓋茨,英特爾、微軟共同終結了前一個王者IBM的壟斷地位,成為PC世界新的國王,進入價值鏈頂端。至今,PC行業中無人能打破Windows加Intel的Wintel模式。
“硅谷的許多資深人士和許多(風險資本家)都曾為他工作過,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職業生涯就是硅谷的發展故事。”戴維·約菲說。
另一方面,安迪·格魯夫淡出一線后,斯坦福商學院兼職教授的工作,讓他的思想和門生依舊遍布硅谷。“以斯坦福技術和斯坦福商學院學生合作為代表,是現在‘商業化’硅谷的特征。”王煜全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安迪·格魯夫1998年卸任英特爾CEO職務,僅擔任英特爾董事長,因為他被查出患了前列腺癌。此后的20多年間,他又患上了帕金森癥,不斷穿越“死亡之谷”,其人生經歷正如他在《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一書中所說的:“穿越戰略轉折點為我們設下的死亡之谷,是一個企業組織必須歷經的最大磨難。”
但英雄和他的時代也會有過去的一天。
雖然當下主要由斯坦福商學院學生組成的“硅谷新貴俱樂部”也受到安迪·格魯夫的巨大影響,英特爾身上也留存著安迪·格魯夫時代的記憶。不過在王煜全看來,無論主流文化和人群,當下的硅谷和安迪·格魯夫時代那個硅谷已經變化了太多。
“我一直講硅谷是‘三個硅谷’。”王煜全說。所謂“第一個硅谷”,是從惠普開始,英特爾延續的“硬件硅谷”,其特點是“工程師文化”,安迪·格魯夫式對技術、工程的“偏執狂”;“第二個硅谷”是以微軟、谷歌、Facebook等為代表的“軟件互聯網硅谷”,離經叛道、希望構造虛擬世界的理想王國,但正在被馴化。
而“第三個硅谷”,是“斯坦福圍繞的硅谷”,“美國的創新現在大量依托高校科技,不管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其實都是高校技術成果的體現。恰巧斯坦福是其中一個非常優秀的高校。所以你會看到,硅谷前兩代從斯坦福畢業的創業者并不多,現在突然驟增。”王煜全說。
“硅谷還是有很多踏踏實實的工程師,但現在的工程師已經不再像過去,以前這批人就像‘宅男’,天天在家里玩兒命干,現在的工程師更加社會化了——習慣了西服筆挺,做好看的PPT,到處去講改變世界的故事。”王煜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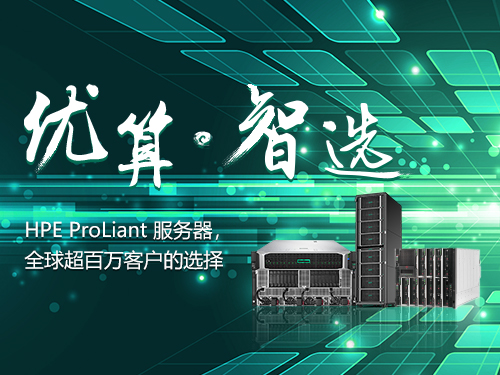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