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YZONE特寫,大時代惘聞錄
幾十萬人,有幾十萬張臉、幾十萬種個體意志,即便放在中國娛樂業(yè)時間軸里做縱向對比,這也是一支龐大、復雜的組織,甚至稱得上是一個現(xiàn)代社會學里的標志性事物。
文 | 連冉
編輯 | 董力瀚
圖片設計 | 李斌才
采訪 | 連冉 董力瀚
虹橋T2 VIP通道出口,吳亦凡出現(xiàn)了。黑色保姆車就停在路邊,他本可以徑直走過去,直接乘車離開。
不過他沒有,而是側身走向了林光宇所在的人群。她們已經(jīng)等了兩個小時。可能吳亦凡就這么走了,她原本想。「其實在國外接機更容易點,他有時會走普通出口,更可能跟粉絲說上話」,林光宇說,「國內(nèi)就不好說了,也有等幾個小時接不到人的情況。」
她們一起等在通道的另一面,在圍欄外喊吳亦凡的名字,吳亦凡走來打招呼,她們又為他唱生日快樂歌,他完整聽完,向人群緩慢地鞠了一躬,表達謝意,才一邊揮手跟大家告別一邊離開。
就接機來說,這次算很有收獲,這收獲讓林光宇覺得感動,她想,吳亦凡完全可以直接上車走人的,可他沒有,而這種小事正體現(xiàn)了偶像的教養(yǎng),「也覺得他是特別溫柔的人。」
和林光宇一樣,和所有其他偶像的粉絲一樣,她們樂于從吳亦凡的行為細節(jié)里,觀察其優(yōu)秀的特質(zhì),并藉此進一步確認、強化自己的崇拜與追求。
吳亦凡有多少粉絲?按江湖傳言,這位偶像藝人身后歷來有個「粉絲三千萬」的說法;按社交網(wǎng)絡數(shù)據(jù),本季《中國新說唱》收官當天,他的微博粉絲突破四千萬;按照粉絲內(nèi)部觀察,其中保持日常關注并頻繁參與團體協(xié)作的忠粉,在數(shù)十萬量級。
幾十萬人,有幾十萬張臉、幾十萬種個體意志,即便放在中國娛樂業(yè)時間軸里做縱向對比,這也是一支相當龐大、復雜的組織,甚至稱得上是一個現(xiàn)代社會學里的標志性事物。
她們通過社交平臺構建了組織結構,它好像一座精密的巨型鐘表,無數(shù)個光澤各異的金屬齒輪交錯排列,咬合,轉動,它承擔著巨大的信息吞吐量,循環(huán)流轉、調(diào)度著每個節(jié)點,并最終向外輸出最為恰當?shù)募w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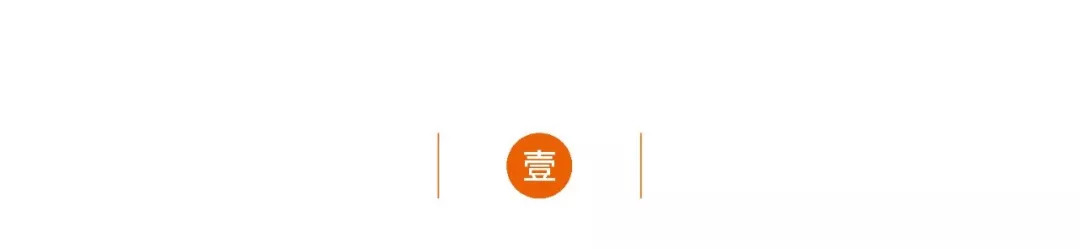
「拒絕一切碰瓷」
先從7月末與虎撲的故事說起。
那天下午,虎撲社區(qū)微博管理員給此次與吳亦凡粉絲的爭論下了定義,一個口號式的定義,叫「戰(zhàn)爭」,「這是一場戰(zhàn)爭,JRS(虎撲網(wǎng)友)準備好了嗎?」
此前一天,吳亦凡「反黑組」在微博發(fā)布關于虎撲網(wǎng)帖的舉報鏈接,發(fā)酵一整天后,步行街論壇被點燃,社區(qū)陷入狂歡,當天有數(shù)百條網(wǎng)帖跟進討論,其中不乏「大字報」式的檄文,甚至連點亮功能都被修改為「skr」——這也可以視其為修筑戰(zhàn)前防御工事。
其間,曾經(jīng)有數(shù)個帖子提出過對虎撲官方態(tài)度的質(zhì)疑,有人不理解,為何論壇官方出面助推沖突,但這些討論并未引起波瀾,很快就淹沒在針對吳亦凡和梅格妮(吳亦凡粉絲,同「每個你」)們的聲討浪潮里了。
當時,多數(shù)JRS認為,「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他們要思量的核心在于己方網(wǎng)友人數(shù)、戰(zhàn)力如何,以及虎撲官方的答題等防御機制是否有效。
只是現(xiàn)實蹊蹺得很,吳亦凡粉絲反應激烈,卻沒有在虎撲現(xiàn)身。
田沁從練習生時期開始追吳亦凡,三年前,還在讀高中的她去北京工人體育館參加偶像生日會,同場的是一群同年齡層的年輕女孩。
在耀眼的氣氛里,田沁覺得感動脹滿胸臆,她也意外地意識到,這些同齡人在網(wǎng)絡前后呈現(xiàn)出巨大的分裂感。
2018超級企鵝聯(lián)盟明星賽紅藍大戰(zhàn),球迷中有人舉起畫幅聲援吳亦凡(圖源東方IC)
旁邊幾位女孩舉著沉甸甸的「凡」字燈牌,瑩黃色的光映著暗面一排凍得通紅的笑臉,原來她們生活里是溫順的,而一旦遇到吳亦凡在網(wǎng)絡上遭遇「攻擊」,她們中有些人便會立刻披上微博小號外衣,化身「準備惡斗的小公雞」,咄咄逼人問候對面。
按這個邏輯,與虎撲的沖突,自然應當是一個令她們無法容忍的事件。
可她們沒有出現(xiàn),這顯然是悖論,背后是整個「虎撲&吳亦凡」事件中最值得玩味的邏輯之一:粉絲們用集體意志的貫徹消解了個體情緒。
所有人枕戈待旦之時,吳亦凡粉絲的怒火與虎撲論壇完全錯配,很少有梅格妮在虎撲發(fā)帖。
一位吳亦凡粉絲對《創(chuàng)業(yè)邦》說,當晚她所在的所有QQ群里都在號召粉絲們「不要直接在虎撲評論,控評去微博舉報」。
這些行為背后的理由之一是微博作為更加開放的社交平臺,天然是粉絲們的主戰(zhàn)場;理由之二,是拒絕給虎撲提供新增注冊用戶與點擊量。
「不論是虎撲,還是其他流量明星,我們拒絕一切碰瓷」,在前線追了多年的站姐鐘謹說,因為吳亦凡早已是「流量Top」,那么在所有與其有關的博弈中,首先要杜絕被有心人蹭熱度與流量。
在這些事情上,她們習慣于對每一次沖突里的每一個參與方的行為做深度思考,這也直接決定了雙方后續(xù)的敵友關系界定:比如此前一檔說唱節(jié)目導師由某位歌手更換為吳亦凡,導致雙方粉絲「正常罵戰(zhàn)」,其間,對方工作室向吳亦凡的某幾位大粉發(fā)出了律師函,「大家就一臉懵,還有這種新式碰瓷手法嗎?」
在整個事件里,另一個焦點角色虎撲始終對此事諱莫如深,并謝絕了采訪邀約。
「沒法兒摘濾鏡」
和所有接受采訪的女孩一樣,談話伊始,吳亦凡的大粉鐘謹就表了個態(tài),說她「沒法兒摘濾鏡」,也就是說,她不可能以任何不傾向于吳亦凡權益的立場來談論問題。
對粉絲來說,這種濾鏡同時又像一卷皮尺,用來衡量尺度,尋找分寸。
要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娛樂圈的每一番爭斗背后,都有多方利益、人情糾葛,作為粉絲中的KOL,鐘謹覺得,復盤推演是自己的職責,她要清晰、準確地維護偶像的權益,首先必須厘清臺面幕后各方的利益關系。
吳曉益追了吳亦凡多年,現(xiàn)在從事藝人經(jīng)濟工作。這也算得從粉絲層面向藝人經(jīng)紀行業(yè)輸出方法論的經(jīng)典案例,在她看來,虎撲事件中人為操作的理由十分充分:綜藝節(jié)目制作方與平臺為求熱度,營造或借勢沖突是常見的事,此外,很多宣傳團隊也會引導負面事件轉向正面。
私下推論不是公斷,對她們來說,結論無須苛求嚴謹,只求清晰,所以結果倒推的辦法就很好使。如果把虎撲事件視為一次營銷,那得說是玩得成功又高級,卷入其中的虎撲、吳亦凡、愛奇藝、參賽歌手甚至是販賣虎撲賬號的商家,均是流量和熱度的受益方,但鐘謹堅持認為事有蹊蹺,「如果虎撲真心不希望節(jié)目有流量的話,為什么要助推「skr」這個熱詞?」
另一位受訪的粉絲則認為,由吳亦凡微博稱「不知動了誰的奶酪」來看,事件背后可能是由娛樂業(yè)同行競爭驅動。
在條分縷析的過程里,濾鏡的存在意義就是,提供方向感。
盡管吳亦凡當期發(fā)的歌同樣獲取了很高的播放量,但在鐘謹們看來,她們的偶像仍然是整個事件中唯一的受害方,因為損失了口碑。同時,很多梅格妮也對吳亦凡工作室不甚滿意,「他們發(fā)了個聲明就消失了。」
而吳亦凡的表現(xiàn),則被認為非常得體。甚至其微博發(fā)聲,并發(fā)表Diss Track,在吳曉益眼中也是某種義舉,「他覺得一幫維護者我的姑娘,因為我受了委屈,我看不下去,所以就站了出來。」
只是,工作室官方態(tài)度中的晦暗不明之處,以及客觀上獲取的歌曲流量紅利,是否也意味著,其中也有多方達成默契的可能性?鐘謹則明確拒絕將此納入考量,「我們粉絲其實只能知道工作室希望我們知道的事情,也只做到粉絲能做的。」
吳亦凡的微博粉絲數(shù)量已經(jīng)超過4000萬,按照鐘謹?shù)挠^察,其中日常持續(xù)打卡、活躍度較高的「唯飯(只追某一明星的忠粉)」約在數(shù)十萬量級。
她們懂公關、運營、流量與組織管理,也有充足的購買力,尤其令人驚訝的是,這個以年輕女性為絕對主導的龐大社群,在很多個面向上展現(xiàn)出了強大的自覺性,與虎撲的這一場沖突中,她們展現(xiàn)的應對策略與思考方式,正是一個鮮明的例證。
「進入游戲」
和吳亦凡星途上歷經(jīng)的雜駁曲折不同,其粉絲群體從練習生時期發(fā)端,整個組織結構的成長是線性的、流動的。如今,通過貼吧、微博、QQ、豆瓣等社交平臺及工具,有數(shù)十萬人將她們的日常交匯起來。
她們絕大多數(shù)是女性,介入互相的生活不算多。有人家境優(yōu)渥各處跟飛,有人窮到湊不出機票錢,有人為偶像學了各項技能,有人追星追到學業(yè)荒廢,有人在微博卷著鄉(xiāng)罵做潑婦、口無遮攔,有人在校園裙角飛揚談戀愛、甜美可人,有人出入映著晴空的高級寫字樓,工作體面,有人雙眼前掛著厚厚瓶底,點著下巴背單詞……幾十萬人,有幾十萬張臉、幾十萬種個體意志,即便放在中國娛樂業(yè)時間軸里做縱向對比,這也是個空前龐大、復雜的組織,甚至稱得上是一個現(xiàn)代社會學里的標志性事物。
她們并未遵循任何組織管理理念或者指導,每個枝節(jié)都是自由生長而來。作為藝人,在練習生時期需要面臨大量的平行競爭,而經(jīng)紀公司幾乎不會做任何資源配置與傾斜。
以吳亦凡、鹿晗等人為例,尚未出道時,便有粉絲在宣發(fā)等事務性工作上投入資金、精力與支持,到2014年吳亦凡歸國,他的粉絲們由其個人業(yè)務需求出發(fā),開始自發(fā)地把個體的、抽象的熱情整合起來,再行分發(fā),以構建更加有效的組織結構。
按照鐘謹?shù)睦斫猓瑓且喾驳姆劢z之前與虎撲用戶「河水不犯井水」,如果非要說有交集,也頂多是吳本人好打籃球,打過幾場All-Star名人賽,引起過虎撲關注。
此次微博名為「銀河鯊魚護衛(wèi)隊」的站姐將虎撲步行街上與吳亦凡相關的負面貼子地址、舉報原因與舉報方法詳細整理后被虎撲發(fā)現(xiàn),引起擦槍走火,該微博上述行為屬于吳亦凡粉絲的「反黑組」日常,此事也可以理解為,外界偶然窺見這臺機器的運作時,由雙方認知差異,所引發(fā)的摩擦。
在成體系的粉絲組織結構中,反黑組隸屬于后臺職能部門,與其平行的還有資源組、數(shù)據(jù)組、翻譯組等,每天整理與偶像相關的負面信息,集中發(fā)布在某些平臺,并把「控評」工作分發(fā)下去,也是反黑組最主要的常規(guī)工作。而少數(shù)工作、課業(yè)不那么繁重,經(jīng)濟條件較好的粉絲則更多會「跑前線」,在機場、工作地拿到大量第一手的照片、資訊,并經(jīng)營微博等站點,被稱為「站姐」。
(按類型、職能與屬性等不同維度劃分粉絲群體)
但是對經(jīng)營公共人物品牌來說,反黑只能守住下限,真正引導其在更高層級的商業(yè)價值上博弈的,還是流量數(shù)據(jù)。
數(shù)據(jù)背后有代價,無論你是否認同,如果要進入這場關乎流量的商業(yè)游戲,必須要遵守規(guī)則,要去「運做」,而這也是所謂「數(shù)據(jù)組」的存在意義。
「廢物」,談到流量數(shù)據(jù),吳曉益干脆地甩出來這兩個字,在她看來,數(shù)值本身沒有什么意義。但在娛樂圈尤其是時尚圈內(nèi),市場對藝人相關數(shù)據(jù)很是看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偶像的帶貨能力。
為了給偶像撕資源,粉絲常常大動干戈地做/買數(shù)據(jù)。這包括但不限于轉評偶像的微博,成果會呈現(xiàn)在微博榜單;若偶像出歌則打歌,整理音源數(shù)據(jù),包括排名,主打,MV播放量等數(shù)據(jù);幫偶像打榜投票,包括明星勢力榜、百度百科明星人氣榜、百度搜索風云榜、尋藝新媒體藝人指數(shù)榜、微熱點熱度榜、超級話題、百度貼吧等諸多榜單。
隨著游戲進程深入,規(guī)則也變得越來越難。
例如,在運作微博轉發(fā)量時,只有不太受到關注的小藝人才可能購買微博大號的轉發(fā)做數(shù)據(jù),反而越是當紅的藝人,越需要精細化運營。目前每個微博小號往往轉發(fā)40次左右就會被封號,因此「水軍」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可靠,而藝人社交平臺最終數(shù)據(jù)的高低,仍然取決于其粉絲團的人數(shù)、忠誠度、管理水準、運營效率等硬實力。
在應援的執(zhí)行上,則有更加細化、明確的策略出臺來應對每一件事務。10月19日,吳亦凡的新專輯開啟預售,但微博上多個站子都在呼吁粉絲「不要參與Pre-order」。
理由在于藝人「國際路線」的定位。對吳亦凡來說,要發(fā)新歌,最重要的成績單是iTunes美國總榜和Billboard榜單,那么就必須吃透榜單規(guī)則,按規(guī)則出牌。微博上,名為「FanGalaxy_凡騎吧」的站子發(fā)帖解釋,「正式發(fā)行的日期是11.2,我們沖首日及首周的成績最重要。一個號只能買一次。你確定你的號一定在11.2或11.2之后一周內(nèi)買到即可。」
盡管品牌方對其中某些數(shù)據(jù)的水分含量心知肚明,但他們也認可大部分數(shù)據(jù)、榜單成績具有相當?shù)膮⒖純r值。而有些數(shù)據(jù)也仿佛失去了坐標軸的曲線,它們的相互攀比、競爭,本質(zhì)上也是一種相互依存,只有借助彼此為坐標,方才使得自身有存在價值。
粉絲生意經(jīng)
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鐘謹總是處于短途的「在路上」。她會很早到公司,到前臺「嘟」地打卡,再掉頭去機場,奔赴吳亦凡開工的城市,為偶像站臺2小時,現(xiàn)場抓取照片、資訊,當日再折返回居住城市,回單位打卡。以至于,三個月間便刷完了一張存著十萬元的銀行卡。
有些站姐更是會跟著吳亦凡「滿世界飛」,她們是粉絲中距離偶像最近的人,不僅與工作人員溝通密切,甚至和偶像本人也有著一定的交往。在整臺機器中,由于承擔著一線的內(nèi)容分發(fā)職能,站姐們事實上成為一個個內(nèi)部流量流轉的節(jié)點。但與社交網(wǎng)絡上多數(shù)的流量節(jié)點相比,吳亦凡粉絲站子的商業(yè)變現(xiàn)又十分有限。
鐘謹很早便開設了站子,但她并不愿透露自己所管理的賬號名稱,也不止她,不公開表明身份,是經(jīng)營站子的一個暗線規(guī)則。一方面,這是粉絲,尤其是粉絲KOL對自己真實生活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免去某些麻煩。
麻煩的可能性,就潛藏在商業(yè)模式里,因為某種意義上,這是粉絲利用偶像的資源反向變現(xiàn)。
2017超級企鵝籃球名人賽紅毯儀式,粉絲在場外翹首以待吳亦凡
除了貼吧之外,微博站子可以說是粉絲流量最集中的區(qū)域。在網(wǎng)絡上,流量天然是個變現(xiàn)工具,很多站姐會將手里資源藉此變現(xiàn),其中,PB(即photobook,粉絲制作的圖片寫真書)是最常見的一種產(chǎn)品形式。
一位豆瓣網(wǎng)友曾解讀過PB的生意經(jīng),首先其成本低廉,一本mini PB,B5大小,30P,500本起印,成本5元/本,1000本起印的話,則為3元/本,2000本起印,更可以達到2.5元/本。但站姐出售PB,最少也要數(shù)百元起。
據(jù)該網(wǎng)友稱,PB本身就處于灰色地帶,一般都是在粉圈內(nèi)低調(diào)出售。其灰色部分在于多個層面,例如私拍的明星照片多數(shù)未獲商用授權,助長跟蹤、偷拍風氣,不時有圈錢跑路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并且最重要的一點是,PB本身就是典型的非法出版物。
但由于又承擔著信息交互、維持粉絲群體熱度、以及補貼站姐營運成本等職能,PB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暗線規(guī)則內(nèi),PB始終是被默許的產(chǎn)品,但站姐賣PB賺來的錢,除了補貼成本,余款理應返還為偶像做應援,雖然是個體經(jīng)營賺來的錢,但「私吞」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爬墻(同時追求其他明星藝人)」則更是「重罪」。
這其實也是所有經(jīng)手資金流轉的粉絲面對的課題,要應付整個組織機構內(nèi)無處不在的隱性監(jiān)督。
資金流轉這件事,在一些近年出道的藝人粉絲組織里更加敏感,因為純粹的「集資」行為頻率更高,如果出現(xiàn)大的問題,比如賬目對不上,應援出錯影響藝人形象,這些都會被粉絲「掛」,管理和組織者可能被要求道歉,甚至交出權力,退出組織。
例如,此前鄧倫全球后援會在應援活動里就出了岔子,送至現(xiàn)場的燒餅、水果等物資,被諷刺稱「又貪又蠢,撈錢撈的傻子都知道有問題」。
這件事情的結果是,涉事分會會長、副會長引咎辭職,后援會管理組就地解散并公開招募,承諾公開透明。
有限變現(xiàn)的流量
吳亦凡的粉絲站子里,養(yǎng)不來流量商人。
幾十萬人的關注,為吳亦凡粉絲群交織出一個牢不可破的監(jiān)督機制,在更大范圍內(nèi)杜絕貪腐,同時也隔絕了商業(yè)化個人或機構的介入。質(zhì)言之,懷著純粹的商業(yè)考量,去從事吳亦凡粉絲流量生意的行為,在組織內(nèi)是不被接受的。
即便社交平臺被認為供給的是原生流量,用戶的交互仍然需要以內(nèi)容驅動,因此常年追隨在前線的站姐——在梅格妮中大約只有數(shù)十人——是鏈條中的內(nèi)容分發(fā)肇始點,她們手中的站子,也是流量最為集中的節(jié)點。
換句話說,如果經(jīng)營粉絲的流量生意,開設站子是最適合的路徑,問題在于,這門生意很容易就會被從內(nèi)容入口處掐滅。雖然市場上日常也可以買到一些圖片和消息,但如果不是跑在一線的站姐,很難穩(wěn)定地獲取街拍圖片和資訊等內(nèi)容。

2018年8月,吳亦凡拿獎歸來一臉疲憊,粉絲拉橫幅歡呼歡迎
(圖源東方IC)
「我們作為前線感覺得出來,一個新人進來,我們很快就能知道底細。」
「你只是買圖,從來沒有在現(xiàn)場出現(xiàn)過,我們覺得你不肯為吳亦凡花錢,還想賺錢的話,首先就把你『搞死』。」鐘謹說,「如果一個站子去不了幾次現(xiàn)場,PB卻賣的很勤,大家心里都有數(shù)的。」
吳曉益覺得,這一方面說明了吳亦凡的粉絲更加熱情純粹,另外也是時機使然,「以前大家對這事認知不清晰,沒人想到賣貨能跟應援一起做,而現(xiàn)在圈子已經(jīng)很穩(wěn)固了。」
最近幾年躥升迅猛的新晉藝人粉絲群里,商業(yè)化做得更加通透,由于組織群體仍然在不斷擴張中,持續(xù)出現(xiàn)增量人群,人群意味著紅利,因此有大量空間可以執(zhí)行商業(yè)行為。
以PB為例,吳亦凡的PB,賣到大幾百冊是個不錯的表現(xiàn),對站姐來說,這個數(shù)字能做到盈虧平衡,或小有盈余;而蔡徐坤的PB則全然不同,動輒可賣出幾萬冊,這種小爆款背后,通常意味著數(shù)十萬元的利潤。前不久,蔡徐坤的生日會門票被炒至天價,讓鐘謹直呼沒見過這陣仗,有人捧著三萬五滿世界找門票,就為了見蔡徐坤1小時,「瘋了嗎這是」。
由于正在從事藝人經(jīng)紀工作,吳曉益此前對照自己帶的藝人,做了個蔡徐坤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她發(fā)現(xiàn),在《偶像練習生》上線之后的半年內(nèi),蔡徐坤的各項粉絲數(shù)據(jù)表現(xiàn)堪稱「現(xiàn)象級」,比賽期間4個月粉絲上漲455萬,而比賽結束后又持續(xù)躥升起了100多萬。「太可怕了,難以想象這是個剛出道新人的數(shù)據(jù)。」
此外,在新浪微博的超話中,蔡徐坤的表現(xiàn)也很突出,以2018年10月23日為例,截至上午9時,蔡徐坤在超話位列第1,簽到超過19萬人次,吳亦凡排名24,簽到約4萬人次。
從下半年承接熱度的《創(chuàng)造101》、《SNH48第五屆總選》活動來看,藝人應援更加令人咂舌,盡管曾出現(xiàn)了粉頭卷錢等負面信息,但可集資數(shù)據(jù)一度分別達到了4000萬元和7000萬元。
不過鐘謹認為,吳亦凡的橫向對比,已經(jīng)不在社交網(wǎng)絡這個維度上,「他已經(jīng)不太需要這種數(shù)據(jù)了」。
她認為,吳亦凡的商業(yè)價值已經(jīng)脫離了應援層面,而是集中體現(xiàn)在商業(yè)代言上,即她們經(jīng)常談論的「帶貨能力」。吳亦凡的粉絲的目標是「帶貨王」,執(zhí)行上也很簡單,「送禮當送Burberry、首飾珠寶選BVLGARI,飲料就喝茶π」。2016年10月份,Burberry簽下吳亦凡做代言,次年一季度,亞太地區(qū)零售額實現(xiàn)14%的逆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是吳亦凡「帶貨能力」的體現(xiàn)。
當《創(chuàng)業(yè)邦》問到另一個吳亦凡粉絲關于對比的問題,得到的答案更干脆,「就是藝人和偶像的區(qū)別。」
統(tǒng)一的價值觀
如果我們做出這樣的假設,你也許感到不可思議——你生活在一個擁有數(shù)千家住戶、十余萬人口的高端社區(qū)里,家委會年初動員所有家庭集資建起一座街心公園;三伏天,獲取居民集體簽字同意放棄寵物飼養(yǎng);年末則集體騰退,辟出這塊地皮,建設高爾夫球場……
其實不單在于社區(qū),對于稍微成規(guī)模的人群來說,這種集體意志的高度統(tǒng)一都是不可實現(xiàn),乃至令人倍感荒誕的。
但在網(wǎng)絡上,粉絲間,數(shù)十萬人、數(shù)百萬人卻可以循著某種特殊的情緒去一起實現(xiàn)它,如果我們?nèi)匀粚⒎劢z組織物化為一臺機器去理解的話,你會發(fā)現(xiàn)其高效運轉背后最本質(zhì)的基礎,在于價值判斷的統(tǒng)一。
對與吳亦凡有關的任何事物,在梅格妮的群體間,可以快速消化,實現(xiàn)價值判斷,并以集體的形式輸出反饋。
2015年11月,工體生日會,粉絲專注看向臺上的吳亦凡
有些常用的判斷會形成規(guī)則,比如說,前線的站姐跟著吳亦凡到處跑,在各地錄節(jié)目時為其站臺,是可以被鼓勵的行為,但追私(跟蹤明星的私人行程)則決不可接受——雖然明星本人的航班信息8塊錢就可以在微博上買到。
也有道德層面的約束規(guī)則,比如同時追求兩位明星藝人,是令人特別不齒的事情。
更多的集體判斷,則被高效地應用在具體事件中,例如,前述與虎撲的沖突,以及與某位女藝人的合作,由于存在很大的「被碰瓷」嫌疑,就是必須回避的。對此相對,吳亦凡與劉亦菲的合作又被視為加分項,因為「好看的人就應該跟好看的人在一起」。
這些集體意志潛藏著驅動力,它會受到偶像本人的引導,但也有很多時刻,可以形成反向制約,最常見的標的是指向經(jīng)紀公司與工作室的。
去年吳亦凡工作室不顧粉絲反對,接下了與某女藝人組CP的綜藝節(jié)目,這令鐘謹感到喪氣,在那之前,包括她在內(nèi)的很多站姐都在「瘋狂地給工作室打預防針」,「就說對方慣用的宣傳伎倆就是捆綁男藝人,但是工作室沒有太當回事,后來果然被猜中了,再去控制就已經(jīng)來不及了。」
粉絲圈里常年流傳著類似故事:A工作室公開發(fā)信為工作失當?shù)狼福籅團隊發(fā)錯通稿;C藝人在直播中遭強吻,工作室兩天后才做出反饋;D藝人微博管理員發(fā)錯賑災文案等等。甚至有媒體人發(fā)文反問,「世界上有『讓粉絲滿意的藝人工作室』這種生物嗎?」
粉絲往往會與工作室陷入一個長久的博弈、合作又制衡著的關系當中去,而粉絲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個市場的買方亦或合約中的甲方,雖然內(nèi)含一些自律條款,但更多時候,還是會將壓力和焦點集中在藝人工作室上,用粉絲的熱情去衡量對方的工作,并希望得到匹配自己付出的表現(xiàn)。
「你不可能指望經(jīng)紀團隊做好所有事,我們都會懷著一腔熱情幫忙,公關需要成本,但粉絲是沒有成本的。」一位站姐告訴《創(chuàng)業(yè)邦》。
「我們的判斷標準是統(tǒng)一的,就是對吳亦凡好」,她說,「沒有看上去還行,看上去還行已經(jīng)算不好了,就必須得完美。」
「大家不明白」
無論是林光宇、吳曉益還是鐘謹,她們對吳亦凡的情感表達,大多局限在微博、貼吧這類開放平臺上。現(xiàn)實生活中,職場里,甚至在封閉的社交網(wǎng)絡——例如微信朋友圈——當中,她們都不太會展露這一面。
她們清楚地知道,在公共話語體系中,粉絲是一個天然的偏見載體。
「粉絲可能在大部分人眼里算是異類,因為大家不明白,我們?yōu)槭裁匆鲞@樣一些事情,為什么要一直追著那個與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林光宇說。
極端個案也一直存在。今年13歲的陳畫,為了追吳亦凡的行程,不聲不響刷掉了媽媽2萬元的信用卡——在家庭貸款尚未還完,信用卡為應急之用的情況下——這也造成了家庭關系緊張。有些粉絲好友不時會為其轉賬應急。她之前已經(jīng)瞞著家里去看過吳亦凡參加的跨年演唱會,而如果信用卡的事沒有暴露,此時她應該又在另一個現(xiàn)場。
其實粉絲、偏見甚至極端案例都不是新鮮事物。上世紀60年代,英美等西方社會人群對披頭士團隊的狂熱,體現(xiàn)為成千上萬的女性粉絲的狂熱包圍,最終留下了一個看上去詭異多變、難以描摹的詞匯「Beatlemania(披頭士狂熱)」,一篇名為《 Beatlemania:Girls Just Want Have Fun 》的文章寫道,1964年,穿著百慕大式短褲、預科生的高領寬松上衣,梳著蓬松發(fā)式的年輕女孩們,一邊沖向警戒線,一邊呼喊著「我愛林戈(Ringo Starr)」。
在上世紀60年代,這被認為是「史無前例的文化現(xiàn)象」。美國塔爾薩大學傳播系教授朱莉·詹森曾分析過粉絲被「污名化」和遭到社會歧視的原因,她認為,極端粉絲行為隱含著公眾對現(xiàn)代生活的一種批判,粉絲身份本質(zhì)上是對這種孤立的、原子化的現(xiàn)代生活的一種心理補償。
半個世紀過去后,現(xiàn)代生活的意義變得更加未知。與當初的Beatlemania相比,粉絲文化這種社會現(xiàn)象,在市場化的作用下,套上粉絲經(jīng)濟的皮囊,也似乎變得更加穩(wěn)定、可控。對于粉絲個體來說,也在集體意志下,更多地脫離那些極端的表現(xiàn)形式。
粉絲們追求這種平衡感,但并不期待理解,林光宇說,她從未期待讓家人朋友明白自己為什么追星,「你不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永遠不知道別人為什么要做這件事情。」
但平衡的存在是很微妙的。在澎湃新聞的一次采訪中,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當?shù)却呐冊诨璋抵锌吹絽且喾驳募粲皶r,「一排排臉整齊地貼在玻璃上」,然后是吳亦凡的沉默,「多可憐啊,她們」,他暫停了采訪,向窗外輕輕地搖了搖手機,隨即尖叫聲和閃光燈一齊瘋狂閃現(xiàn)。
鐘謹記得,就是這句話,造成了一批人「脫粉」。她為吳亦凡辯白,「他本意不是這樣,本意是心疼大家在等他,可是那句話發(fā)出來,就有種『我看不起你們』的意思,話術這東西……」
吳曉益補充,「他本人對于中文理解不是很好,稿件審核一般是給到團隊,但可能團隊也沒能意識到這句話里的不妥之處,而且如果挑的太細,還可能被對方覺得耍大牌吧。」
偶像與粉絲之間的關系,從來刀尖舔糖,堅固更脆弱。她們?yōu)榕枷窀冻觯冯S他愛護他,在他出現(xiàn)負面消息時堅定地站在他身后,卻在某些時刻,抵擋不住一句話里行間的誤解。
粉絲文化仍然在迅速演化。在工業(yè)化過程中,在某些時刻,偶像作為一種文化產(chǎn)品,高速的迭代會令某些局部的現(xiàn)實失衡,以至于呈現(xiàn)得愈加魔幻。
最近聽來的一個故事,讓林光宇頭緒繁多,又覺得頗有意味:幾位追前線的粉絲,在一架航班上偶遇,面面相覷,竟有些尷尬,因為她們意外地發(fā)現(xiàn),與此前一起追的某次行程相比,粉絲仍是那幾位,保鏢仍是那幾位,只是前面頭等艙的那位偶像,換人了。
而鐘謹最近則奇妙地發(fā)現(xiàn)前線出現(xiàn)了許多新面孔,其中不乏穿校服的小姑娘。前段時間,在《中國新說唱》現(xiàn)場,她能認出的也只有兩個相熟的面龐,其他人都看著陌生。
新粉進來多是由于電影、新歌與節(jié)目的吸引,去年的《中國有嘻哈》可謂是功不可沒。
截至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時,吳亦凡最新的微博粉絲數(shù)為4277萬。他的后援組織疆界依然在持續(xù)擴張。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502049343號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