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所在的團隊為一家車貸公司搭建了一套信審數據模型,該模型可以根據貸款申請者的數據自動預測其在未來能否按時還款,決定是否通過用戶的貸款申請。
相比人工信審,模型預測是全自動的機器過程,在保證判斷準確率的前提下,它能為公司節省大量的人力成本。
項目在客戶的工作地點開展,我們的工位處于一個信審專區,周圍是大量的信審工作人員,他們每天的工作是審核貸款申請者的資料,聯系申請者核實信息,工作間隙,我們總能聽到有趣的對話:
信審員:“你有幾個兒子?”
貸款申請者:“三個。”
信審員:“剛剛打電話給你老婆,她說你們只有兩個兒子,這是怎么回事?”
貸款申請者身旁傳來竊竊私語……
信審員:“你旁邊的人是誰啊?你有幾個兒子還需要別人來提醒你?”
……
對話進行到這里時,信審人員會在系統內記錄下該申請者和配偶提供的信息不一致,存在可能的騙貸行為,這將成為該申請者能否被成功授信的“減分項”。
雖然目的均為實現快速、準確的信貸審核,但數據建模的工作邏輯與人工審核存在明顯的差異。數據分析專家面對的是一串串數字,而業務人員面對的是鮮活的申請者。
數據分析出發點所有客戶的申請資料,包括此人性別、年齡、資產情況等基本信息,以及一些來自第三方平臺的風險數據(如該申請者有無犯罪記錄),簡單地說,我們工作的出發點是一張Excel表格。
反觀另一面,信貸審核人員在處理每筆信貸業務時,他們除了面對每個申請者的具體信息,還會通過電話核實申請者的身份,最終作出人工決策。

數據表格是分析師們每天的工作伙伴
初入數據行業時,我以為只要玩轉手中各種復雜的表格,寫一手漂亮的建模代碼,從透視表中找到有趣的發現,就足以成就一個讓客戶滿意的項目。
然而,老板在入職第一天就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大數據是有局限性的,它無法替代你對真實業務的體會,這也是我們為何要駐場工作。”
在客戶的呼叫中心駐場1個多月后,我似乎明白了老板掛在嘴邊的這種“體會”。
大數據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它將關于你的一切量化為很多數據標簽,然后將它們存儲在表格里,比如你的性別是男性,今天打車回家花了30元,周末玩了兩小時王者榮耀。
大數據的優勢很明顯,它具有一個對所有人通用的結構,每個用戶這些維度的數據都會被記錄在表格中,淘寶知道每個用戶的雙11消費能力,今日頭條對你感興趣的新聞了如指掌,信貸公司記載了你過往的信用記錄。
然而,大數據的不足之處在于,它僅僅是對世界的一個切片,對于切片之外的事物一無所知。
面試官面試新員工時,首先會查看申請者的簡歷,簡歷上的教育背景、工作經驗、語言能力是以固定結構記錄的數據,然而申請者在面試中給予面試官的感受,比如她是氣場強大的女神還是平易近人的萌妹子,大數據則無法給予答案。
在最近的項目中,我們通過數據發現那些教育程度較高的貸款申請者更容易在未來逾期還款,這聽上去有些違背常理,然而精通業務的經理告訴我們這是合理的現象,那些所謂的高學歷是申請者在填寫表格時編造的。后者并不是大數據能夠捕捉的行為,然而對理解申請者的行為至關重要。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的團隊在做出重要投資決策時,他們不僅僅關注能被寫進表格的金融數據,同時親自前往歐洲各地,在當地的酒吧與人們聊天,了解未來可能的宏觀政策變化,索羅斯甚至依賴自己的背痛預判可能的風險。這些無法被標準地量化,甚至聽上去有些荒謬的決策標準卻成就了他們在1992年9月的“黑色星期三”狙擊英鎊,幾周內賺取11億美元的空前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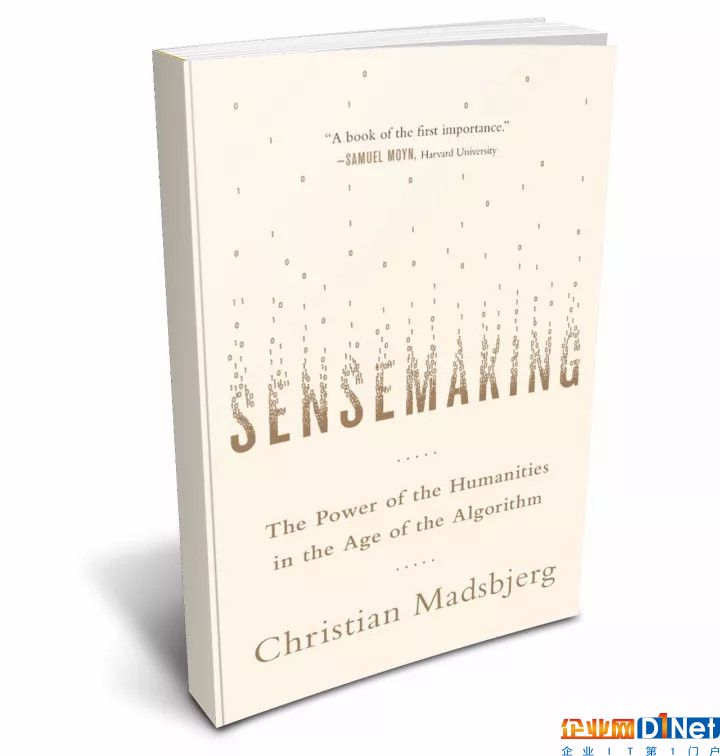
咨詢顧問Christian Madsbjerg的《意會:算法時代人文科學的力量》一書是本文的主要參考書目,該書目前暫無中文版
通常,我們可以把人類認識世界的途徑分為兩種:
一種是如今家喻戶曉的大數據;
另一種則是一直長久存在,卻往往在這個時代被我們忽視的“厚數據”。如果將大數據比作對客觀世界的標準化切片,厚數據則是我們在每個獨特場景的深度感知。
簡歷上的文字是大數據,而面試官對申請者的感覺是厚數據;表格中教育程度一列等于“大學”是大數據,而填寫者在背后的偽裝是厚數據;股票、匯率的歷史走勢是大數據,而酒吧人們的閑聊和索羅斯的背痛是厚數據。
大數據的不足之處在于它缺乏厚數據攜帶的場景。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提出了“存在”(being)這一概念,它指的是世間萬物存在的場景(context),我們對于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能將其孤立為一個元素,而是應考慮這個元素所處的具體場景,以及它與其它元素的相互關系。
海德格爾等人在他們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中對這個概念進行了更詳細的闡釋,現象學的目的在于描述事物真實存在的方式,而不是我們覺得他們應該存在的方式,而事物“真實存在的方式”必然離不開它所處的場景,而不是像大數據那樣對現實進行標準化的切片。
需要注意的是,現象學中的“真實存在”,并不是指這件事必須在客觀上是正確的,比如“世界上只有男和女兩種性別”,而是當我們在某一場景下聽到一個現象學的描述,被問及“你覺得是這樣嗎?”時,我們會點頭表示同意。
同樣的一杯紅酒,在點亮燭光的法國餐廳與嘈雜的辦公桌前飲用,注定是不一樣的感受,雖然它們的化學質地是相同的。
同樣是一個小時,在思修課堂和情人坡度過,必然是不同的長度,雖然它們的自然屬性沒有差異。
兩名被數據標記有存在犯罪記錄的貸款申請者,雖然數據將它們一視同仁,然而一位只是過失的交通肇事,另一位則有搶劫銀行的前科,他們在未來的還款能力或許大相徑庭。
身為數據工作者,當然希望數據和算法能盡可能多地代替人類的工作,但正如我們在項目中看到的,現實并非如此,僅僅面對數據和算法并無法洞察每個申請者所處的獨特場景。機器學習與人類決策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的關系。
這也是為什么,數據分析師們一定要駐場工作,因為只有像信審專員那樣身處業務前線,才能對那些貸款的申請者形成更加深刻的體會。
之所以與大家分享場景、厚數據、現象學這些概念,是因為在這個大數據概念傳遍街頭巷尾的時代,我們極易選擇用簡單的數據標簽衡量一切:
選擇去哪家餐館,只看大眾點評的總體評分,并不在意網友的大段評論。
決定在哪里讀大學,先看學校的綜合及專業排名,不在乎學長學姐們分享的體會。
想了解用戶對產品的滿意度,只要求1000人在問卷上打分,不會深度訪談用戶使用產品時的具體想法和感受。
后者事實上代表了一種以現象學為基礎的“文科思維”,即我們只關注每個獨特場景下的主觀體驗,不會嘗試將許多場景標準化,然后貼上統一的數據標簽。
研究文科思維的專家Christian Madsbjerg認為文科思維是培養我們對外界的敏感度的重要途徑,所謂的敏感度,指的是我們察覺事物間微妙差別的能力。正如兩杯紅酒,在不同地點的1小時,兩名數據畫像相同的申請者,辨別它們之間的差異需要的正是文科思維。
Madsbjerg指出學習諸如藝術、歷史、哲學、社會學、人類學這些人文學科是培養文科思維的重要手段。因為這些學科中存在大量基于具體場景的思考和感知,比如藝術課教你欣賞達芬奇的作品,社會學家擅長消費者深度訪談,人類學家喜歡實地觀察原始部落等,它們不會教你如何將世界編碼成一張數據表格,卻能培養你洞察世間微妙區別的能力。
前段時間看了《看不見的客人》,這是一部懸疑劇,劇情圍繞一名成功的銀行家與一名女律師之間的對話展開,女律師試圖幫助銀行家擺脫殺人的罪名,但殊不知她就是殺人案中被害者的母親。

《看不見的客人》中的女律師
與我一起看電影的小悶同學在女律師出場時脫口而出:“我感覺這個律師就是他媽媽。”她的感覺驚人的準確。
電影結束我問小悶,她是如何做出這樣的判斷的,小悶說律師的面部表情看上去很奇怪,不像一名提供專業服務的人,這顯然不是機器學習算法所能實現的。
今天的內容或許能給小悶對外界的敏感提供解釋:她是一名文科生,而且很喜歡看電影。
最后,與你分享一個關于文科生的好消息。薪酬調研公司PayScale曾做過一項調查,在薪酬排名前20的畢業生專業中,計算機工程、化學工程這樣的理工類專業長期占榜,而社會學、歷史學這樣的人文學科則十分罕見。
這聽上去符合我們的直覺,但如果我們觀察那些收入排在前10%的人,具有政治科學、哲學、戲劇、歷史背景的專業人士則會脫穎而出,寶潔前CEO雷富禮曾對實現商業成功單單提出一條建議:取得一個文科(或稱“自由技藝”)學位(pursue a degree in liberal arts)。
這樣的建議無疑是有道理的,畢竟,真實的世界不是電子表格。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