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網D1Net》12月19日訊
2013年,“棱鏡門”的發生,就像一顆炸彈,在原本平靜的大數據時代下爆炸,“棱鏡門”為人們反思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提供了一個范本,斯諾登潛逃、引渡以及政治庇護這樣的情節增加了戲劇性,卻無礙于反思這個問題的內核。
“謝謝你,斯諾登!”臨近感恩節,一個自由組織為感謝斯諾登公開美國監聽秘密,特地在華盛頓的一輛巴士上打出這樣一幅致謝的廣告。
從2013年6月初,斯諾登揭發美國的“棱鏡門”事件,到九大互聯網巨頭卷入美國監控全球互聯網計劃,再到斯諾登到俄羅斯尋求避難,最后到美國政府斡旋大數據監控是為了所謂的“反恐”。從純技術角度來看,“棱鏡”是一個典型的通過分析海量通訊數據獲取安全情報的大數據案例,但它也引發一個重要的思考: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該何處安放?
經過一段時間的辯論,斯諾登已經被“臉譜化”,一方認為他是公眾隱私權的捍衛者,是自由的守護者;一方認為他是叛國者,是雙面間諜,應該被引渡回國接受審判。當更多的事實披露出來,誰是英雄,誰是罪犯,也會慢慢浮出水面。
震驚源于“小數據”思維
“大數據”基礎已完備
“斯諾登事件讓我驚訝的不是‘棱鏡’計劃本身,而是如此眾多的社會大眾還是小數據’思維,對這個計劃如此驚訝。”這是《大數據時代》一書的作者之一邁爾·史恩伯格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對此全球性事件的反應與感慨。
的確,對當今全球的絕大多數人而言,“大數據”還是個相當陌生的概念,甚至還未曾聽聞,事實上它已悄然而至,從微觀到宏觀,從商業到政治到軍事,鋪天蓋地,無所不在。斯諾登揭露了“棱鏡”,“棱鏡”揭示了“大數據”。
就商業用途而言,今天的谷歌、微軟、惠普等,已完全可以通過它們掌握的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甚至億計的數據,經由“超級計算”,準確推斷消費者的習慣、電影的票房、流感疫情的發展趨勢。商業如此,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用途和潛在利益當然也不遑多讓。
這就是“大數據時代”。
“大數據時代”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一,數以億計的人們,無時無刻,不知不覺地在生產大量數據,每一個人在每一時間每一地點,那怕是一個最不經意的微小行為,就是一個數據。所以,合起來,就是海量的數據。二,數據雖已產生并存在,除非把它“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全數搜集網羅起來,否則沒有意義,這就要靠像“棱鏡”一樣的網絡技術。三,最后一步,就是將海量的數據以超級快的速度加以歸納、計算與分析,這就靠一代又一代推陳出新的超級計算機。第一個基礎是從來就有的,現在,加上了第二與第三,我們就進入到了“大數據時代”了。
正如《紐約時報》所說,斯諾登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因為他使人們看到了,像美國這樣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和情報能力的一個國家,他們會以什么樣的方式來竊取全世界的情報。
D1Net評論:
“棱鏡門”的影響力之大,不僅波及到整個世界,而且時至今日,“棱鏡門”的余音尚在,大數據時代的震感猶在,從另外一個側面來說,“棱鏡門”也在警示著我們在打數據時代下要注重個人隱私的保護,正確運用大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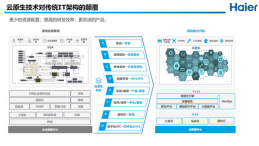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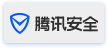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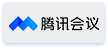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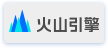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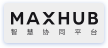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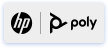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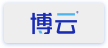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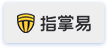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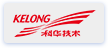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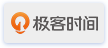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