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計算機技術專家眼中,“云計算”只是一種基于互聯網的計算方式。然而更進一步,“云計算”的實質是對于資源的一種整合方式,可將其稱為“云范式(Cloud Paradigm)”。資源的整合方式往往決定生產效率,也必將引領管理學的革命,并被運用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早在2006年谷歌首席執(zhí)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Emerson Schmidt)提出“云計算”的概念之前,管理領域“云轉型”趨勢已經暗流涌動,其中人力資源管理居于首位。
“自組織”不是終點
人力資源管理的主題永遠是高效整合員工能力以形成相應的組織能力,這直接體現在組織模式的塑造上。而理論和實踐發(fā)展至今,組織模式的范式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
科層化階段 即以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整合人力。這一時期,在戰(zhàn)略需求端,消費能力相對不足,消費需求相對單一,戰(zhàn)略相對單一,產量即是盈利;在人力資源端,管理者和學者普遍將員工界定為“經濟人”,認為人天生厭惡工作,逃避責任,不具備進取心,是由經濟誘因來引發(fā)工作動機的。這種背景下,自上而下地進行分配,嚴格界定每位員工的工作職責,監(jiān)督執(zhí)行,嚴格獎懲就成為了必要。這種范式里,人被作為去個性的工具,其存在是被動式的,組織是高度集權的。
扁平化階段 即盡量消除傳統金字塔結構中的縱向管理層級。這一時期,在戰(zhàn)略需求端,消費能力開始提高,需求開始多元,市場開始出現不確定性,戰(zhàn)略不再是單純的產量,而是需要兼顧消費者偏好;在人力資源端,管理者和學者開始認識到人性的復雜,人性中除了具有“性惡”的一面,更有“合法利己”甚至“無私奉獻”的一面。這種背景下,除了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與約束,自下而上地思考戰(zhàn)略的可能性,即思考在崗位職責內營造氛圍、釋放員工潛能就成為另一種趨勢。人的主觀能動性開始被調動,并在一定業(yè)務范疇內接受組織的分權。
網絡化階段 即以網絡化組織打通資源之間的連接。這一時期,在戰(zhàn)略需求端,消費能力大幅提高,需求多元化越演越烈且變化無常,以至要求滿足極致個性化需求的“體驗經濟”成為普遍現象。任何對消費者偏好的成功揣摩都只能在短期獲利,戰(zhàn)略完全變成了“權變”的結果,因此呼喚一種高度的“柔性(Flexibility)”。在人力資源端,管理者和學者開始意識到人的能力具有高度可塑性。于是,“戰(zhàn)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和“基于能力的人力資源管理”被頻繁提及。
在這個階段,組織需要的似乎是將員工分解為細小的“能力流(Competency Flow)”,通過柔性的網絡化模式進行連接和引導,保證其高效地流向各關鍵業(yè)務領域,支持不斷變化的戰(zhàn)略。這樣,人的主觀能動性被最大程度地調動,形成一種純粹的“自組織”。《維基經濟學:大規(guī)模協作如何改變一切》一書中展示了一種維基工作站(Weki Station)的企業(yè)內協作方式,正是網絡化范式。
繼續(xù)走向云端 即便實現了上述兩次轉型,如今的網絡化范式也不是演化的終點,人力資源管理需要向“云范式”轉型。即將人力資源以網絡狀形態(tài)進行連接,并將網絡以“云計算法則”進行智能化。與“維基式”的網絡化不同之處在于,云是對于網絡的智能化,為“自組織”注入了一種“他組織”的干預。
在網絡化階段,人與人的連接是隨機的,需要在摩擦中尋找秩序,需要通過多次的沖突形成“制度記憶(Institutional Memory)”。盡管這樣的演化結果是更加精巧,但網絡化連接將沖突放大化的效果也如影隨形,演化過程中為消解沖突必然產生大量成本,甚至可能使網絡崩潰。另外,由于不同“小網絡”之間的秩序和標準不統一,“小網絡”融合成為“大網絡”需要漫長的過程,這就限制了網絡威力的發(fā)揮。而云范式為網絡注入了一種經過“優(yōu)化檢驗”的標準化智能(資源分配方式)—云計算法則。不僅使秩序的形成過程成本最小化,也讓小網絡之間的融合更加容易,便于發(fā)揮網絡融合的“乘數效應”。
如果將一個系統分解為主體、載體和客體,那么從不同的視角出發(fā),人力資源的“云轉型”存在三種可能。
主體轉型—“智慧群落”
人力資源系統的主體是人,從這個方向上,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種“云”式的人際連接。
傳統的組織里,人們下意識地會為自己貼上“職位”的標簽。這種“劃地分家”的模式好比一個“權力群落”,保證了組織的穩(wěn)定,消除了生產中的不確定性,卻形成了既有的利益格局,帶來了官僚主義,讓企業(yè)變得笨重而僵化,也使得員工成為一個個循規(guī)蹈矩的“零件”。
一方面,權力群落往往導致企業(yè)缺乏戰(zhàn)略柔性,前線的信息要傳到司令部需要通過無數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不僅貽誤戰(zhàn)機,信息還不一定準確。前線的戰(zhàn)士們只能憑感覺孤軍作戰(zhàn),根本得不到司令部有效的戰(zhàn)略指導,得到的只能是僵化的“標準流程”。另一方面,企業(yè)往往在復制一個又一個“模板”,也因此謀殺了員工的創(chuàng)新能力。新員工在“權力群落”里的生存法則是通過“服從權力來獲得更大的權力”,一切對現有利益格局的挑戰(zhàn)和破壞都將受到懲罰。所以創(chuàng)新的精神被抑制,企業(yè)也變得死氣沉沉。
事實上,員工最了解市場,更不乏創(chuàng)意,最有效的組織模式是直接把這些創(chuàng)意送向關鍵業(yè)務領域,甚至引導這些創(chuàng)意進行碰撞(如“頭腦風暴”),使其變得更加鮮活。人力資源管理需要塑造一種開放、平等的網絡關系,使得交流和協作可以在任何兩個員工之間發(fā)生。在這種關系中,沒有任何的流程、機構和職責,員工用“智慧”標注自己,用智慧進行社交,憑展示贏得激勵,筆者把這種網絡關系稱之為“智慧群落”。
大多企業(yè)中,“智慧群落”往往作為一種虛擬的存在發(fā)揮重要作用。筆者觀察到的一個汽車銷售企業(yè)的案例中,不愿被教條束縛的年輕員工們利用網絡論壇構建了一個虛擬組織,居然像“影子武士”一樣為公司貢獻了讓人叫絕的大量創(chuàng)意。
對于另一類高度知識密集型的企業(yè),“智慧群落”甚至取代了傳統的“權力群落”。一個咨詢企業(yè)的管理者搭建了一個內部的創(chuàng)新市場,引入了外部市場壓力,讓員工將自己研發(fā)的咨詢產品擺上“貨架”進行內部出售,最大程度“維基”了員工的智慧。公司采用了一種另類意義上的“合伙人制”,人人都是合伙人,員工的職位根本不被看重,因為薪酬和權力不是按照職位發(fā)放的。這種新的組織模式“摧毀”了制造層層障礙的中層,打破了部門邊界,權力群落也因此趨于消散。
載體轉型—“維基平臺”
企業(yè)人力資源系統的載體是協作平臺。從這個方向上,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搭建一種“云”式的協作平臺。
傳統的組織里,一方面,塑造人力資源交互平臺的主題是分解自戰(zhàn)略目標的工作任務;另一方面,平臺的運行是依賴于固有的溝通渠道,即報告線或協作關系等。這類平臺的存在,更多是強調穩(wěn)定,卻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員工能力的發(fā)揮。
傳統平臺的第一個問題是主題過于單一。如果將平臺主題視為一種“計算需求”,規(guī)范的工作任務意味著計算需求相對簡單,只需要少數員工的簡單參與。現實在于,當前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需要涉足不同的平臺主題來產生價值,即需要組織向平臺頻繁發(fā)出各類“計算需求”,而管理者的視野和理性都是有限的,能夠發(fā)現的主題和發(fā)出的計算需求必然有限,這就大大減少了企業(yè)獲利的可能性。
第二個問題是平臺的溝通渠道過于狹窄。員工的創(chuàng)意只能通過報告線以特定形式上報,由特定上級決定后才能實施,即使獲準實施,也只能通過與有限協作者的合作來實現。問題是,創(chuàng)意往往是一種轉瞬即逝的靈感,其在萌芽階段都是不成熟的,但往往一兩句話、一兩個詞就能成為創(chuàng)新的來源,而這些創(chuàng)意往往在員工的“頭腦風暴”中變得更加鮮活,何必要求形式?另外,員工之間的認知距離越遠越能夠相互激發(fā)創(chuàng)意,如此看來,何必固定協作伙伴?
事實上,員工作為網絡中的節(jié)點一直存在,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為這些節(jié)點的互動注入各種主題,以及如何為這些節(jié)點建立更廣泛、更便捷的聯系。人力資源管理需要制造一種便于協作的“維基平臺”,主要功能是實現企業(yè)內公共空間的知識記錄和發(fā)布,使得更多的員工可以參與知識的互動。在平臺上,每個員工都是知識的提供者,與進入平臺的任何人進行交流。每個員工同時又是知識的需求者,或是單純基于自身業(yè)務,或是在知識交互中頻繁發(fā)起主題—不同主題代表了不同的計算需求,而平臺上的其他人就會協助其完成“計算”。
這種維基平臺不一定需要高端信息技術的支持。在一家傳統的民用航空企業(yè),其管理人員通過使行動學習、創(chuàng)新論壇、內部講師和課程開發(fā)等活動“慣例化”,為員工之間的跨部門合作建立了渠道。基于合作中的知識交流,大量協作主題得以衍生。就是這樣一個維基平臺,居然攻克了數個以前需要外請咨詢公司來解決的難題。
更加幸運的是,Web 2.0互動社交工具可以使維基平臺更加高效。提供電腦軟件維護服務的企業(yè)—極客小分隊(Geek Squad)就利用社交軟件的溝通渠道,為1.2萬多名分布在美國各地的員工打造了溝通平臺,成功激發(fā)了在知識共享、產品設計、市場推廣等方面的無所不至的創(chuàng)造力。
客體轉型—“知識立方”
人力資源系統的客體就是知識。我們應該考慮如何使知識高效上傳到“云端”,變得更易獲取。
野中郁次郎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知識轉換的螺旋過程模型”認為,個體知識是通過社會化、表述化、綜合化和內在化的四階段循環(huán),并通過個體、團隊到組織三個層面的傳遞成為組織知識。而后,企業(yè)進行知識管理大多遵循這一模型,由此建立組織的“智庫”。但由于種種原因,這類“智庫”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限制,其就像一幅精美的“清明上河圖”,呈現了無數的元素,但就是難以應用。
要解釋這個現象,第一個原因是智庫中的知識缺乏體系性,僅僅是知識片段的無序聚合。隱性知識的傳遞需要人對人,但這樣的傳遞效率顯然不高,因此,如何使隱性知識顯性化并進入智庫就成為了組織思考的問題。大多企業(yè)無非是發(fā)布一個標準模板,讓隱性知識的所有者根據模板進行提煉。這樣的結果是,企業(yè)撰寫了一大堆的文本,并印上了編號,但沒有人清楚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系,沒有人能夠對智庫的文本結構一目了然,更沒有人會期望這些文本能夠支持自身的工作。
第二個原因是智庫中的知識缺乏動態(tài)性,不能支持企業(yè)發(fā)展。智庫的更新最快也要1~2年,在商業(yè)信息瞬息萬變的今天,誰敢于把獲取信息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古書”上呢?況且,沒有比較和爭論,員工怎么敢肯定進入智庫的知識就一定正確呢?
因此,人力資源管理需要打造一個立體動態(tài)的三維“知識立方”,制造一種開放、靈動的立體知識構架,方便所有員工貢獻、分享知識,進行協作,共同呈現知識片段(甚至相互糾錯)及其關聯關系。構架上,一個個知識片段好似“小方塊”,共同搭建成為“大立方”,而“小方塊”本身就可以在立方上以一定的軌跡運動,尋求相互之間的新組合,并被搜索者輕易獲取。
筆者最近訪談了一家央企,其熱衷于通過“互動式培訓”來解決動態(tài)的管理問題。例如,當某個區(qū)域市場內的分銷系統出了問題,其培訓部門就會邀請內外部專家和相關決策線上的管理者進行“互動式培訓”。由外部專家導入專業(yè)知識、內部專家導入集團戰(zhàn)略背景,相關管理者導入決策情境,幾方的互動很快就可以解決問題,問題的答案以文本的形式被記錄,并儲存到企業(yè)智庫中。這種模式強調在知識分享過程中的互動,類似前面談到的知識立方。
有的企業(yè)更加強調知識的動態(tài)性,直接利用維基軟件打造知識立方。國外的部分企業(yè)已經成功實踐了這一理念,但國內的此類成功案例還比較少。
如前文所述,網絡化的人力資源架構制造了“云轉型”的可能性,而真正使“云轉型”變?yōu)楝F實的卻是“他組織”的干預。要施加這種干預,必須找出能夠引導網絡內個體合理釋放資源的“最優(yōu)算法”,即“云計算法則”。這看似神秘,實則簡單,其要義就是根據員工的“人性”導向其行為。
怎樣發(fā)掘人性需求的多維性?管理者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其一,可以用直接的經濟利益進行誘導,如盛大為員工進行知識共享的行為進行積分,并將其兌換為決定經濟收益的“經驗值”。其二,可以利用文化進行誘導,如前面提到的汽車銷售公司,其創(chuàng)新論壇的建立完全是員工不甘于平庸的“反叛之舉”,員工瘋狂貢獻創(chuàng)意只是為了尋找自身的“存在感”。其三,可以利用權力的分配進行誘導,如那家民用航空企業(yè)并沒有為維基平臺注入直接的行為目標,只是通過類似發(fā)布會和文本報告等渠道向中高層管理人員推介研究成果,就立即引起了員工的廣泛呼應,形成了“賽馬”的效果。其四,可以直接引入市場的強激勵,這種模式最為直接有效,如上文的那家咨詢公司,將外部市場對于產品的需求引入了內部市場,使員工的創(chuàng)意都能得到即時的回報,點燃了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熱情。畢竟,還有什么機制對于資源的調配比價格信號更精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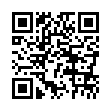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