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多前,“大數據”開始強勢進入傳媒業界、學界視野。不少傳媒人怕“大數據”,因其互聯網基因,亦因其涉及文科生不擅長的“計算”;大勢所趨,又不敢不研究“大數據”。2013年10月中旬,由中國青年報社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聯合主辦的“第四屆全國深度報道研討會”,主題定為“大數據時代的深度報道”。與會嘉賓以平實的語言、可學可用的案例進行了深入探討,有助于從業者平視“大數據”,更新職業技能。
李米勒:
不要恐懼,數據挖掘并不那么難
首先,數據挖掘的宗旨是以數據的形式呈現信息。重要的是,要讓讀者明白數據背后蘊含的意義。如果記者給讀者呈現的數據非常復雜,令人費解,那么這樣的工作毫無意義。
其次,絕大部分記者的數據挖掘都是基于已經公開的數據。比如,通過上市公司財報或政府部門公布的統計數據,來進行數據挖掘。
再次,數據客觀存在,只是需要發掘。三年前,泰格 伍茲在電視直播上公開了他有婚外情的情況,并致歉,整個過程大概有四五分鐘,這是一個非常轟動的事件。佐證其轟動程度的是我同事做的數據挖掘案例:在泰格 伍茲電視直播的前一分鐘,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量達到了當日最低點,而直播之后交易量升至最高點。也就是說,這則新聞對受眾的吸引力大到了連紐交所的交易員都放下了手頭工作。作為一名富有創意的記者,數據挖掘可以讓我們通過更有意思的方式來向讀者展示同樣的新聞。
祝華新:
微博時代的媒體:“黃金小拇指”
近年來政務微博和體制內媒體的法人微博有了大規模的發展。就網上的民間輿論而言,民眾和政府在新聞輿論場的存在中,新聞媒體,特別是媒體的法人微博,將發揮舉足輕重的第三方作用,類似于股東會里的“黃金小拇指”股東,雖然只占5%的股份,卻擁有否決權。
與政務微博相比,新聞媒體與媒體微博具有更強的議程設置能力,能夠制造流行,影響輿論走向。媒體微博的公信力恐怕還在網絡“意見領袖”之上。媒體人經常抱怨缺少足夠的“第四種權力”的話語權,但我們是否能夠審慎地用好這份“話語權”呢?媒體話語權要有利于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表達和公平博弈,增強社會黏合度,而不是加劇政治分歧、進一步撕裂社會。
我們既希望政府公權克服對民意的漠視,同時,媒體也要力戒“道德潔癖”和“智商優越感”,少一點站在道德高地的自以為是,多一點對公眾特別是草根民眾的深切體諒。在互聯網信息真偽難辨、網民情緒經常劍走偏鋒的情況下,新聞媒體不能成為網絡帖文的印刷版。要對網絡信息去偽存真,為網民情緒扶正抑偏。
陳昌鳳:
美國大報的數據新聞案例解析
《華盛頓郵報》曾做過專題策劃“消失的面孔”,專門報道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期間的陣亡者。首頁是陣亡者的肖像,而每張照片點擊后,都可以鏈接到相關的介紹、故事、深度報道。這是《華盛頓郵報》的一個專題,做成了一個App。
《芝加哥論壇報》則整合了芝加哥的犯罪記錄。輸入所在的社區或街道,受眾就可以了解到那里的安全情況、犯罪情況,最近一周的、最近一年的、甚至更久以前的信息都可獲取。無論是超過300美元的偷竊,還是重大犯罪,這里都有記錄,區別僅在于后者會配發故事。這其實已經不僅是新聞報道,而是成為公共服務了。
還有一個關于數據可視化的問題。《華盛頓郵報》曾經做過一張令人吃驚的世界地圖:全球的無神論者生活在哪里。其實只是記者從相關研究者手中獲取了一些數據,然后記者創造性地以地圖的形式展現了這則新聞。
近來,這些全媒體或者多種媒體融合的方式在國內也已經有所嘗試,例如新華社近期操作的“地球綠飄帶”活動,效果絕對超過了任何一種單一的媒體,超鏈接、推進、拉出,四維空間,立體呈現,充分利用了新媒體的特質,報紙是絕對達不到這種效果的。
沈陽:
大數據時代的搜索與聚合
大數據體現的人在各種媒體空間中產生的數據。深度報道是構建出一個媒體中的情境場景的一個人。
要報道一個人,記者可以在谷歌趨勢中搜索其全球關注度,也可以在社交網站中分析。深度報道中還可以利用大量的人物關系進行分析。要分析夏俊峰,在搜索引擎中基于已有的大數據再進行人工篩選。比如說夏俊峰事件中有他兒子的畫。
要把深度報道聚合,有幾個角度的數據要打通。我們有全網的數據、微博的數據、微信的數據、QQ空間、人人網的數據。今年很多新聞當事人都在微博里,包括新浪和騰訊微博,需要把人和文本打通。原來記者95%的工作都是在跟人打交道。隨著數據新聞技術的成熟,可能30%的工作量會移到和人、文本數據打通中。比如,在幾年前搶鹽風潮中,3月14日,搜索“買碘片”返回條數為2058條。3月15日,搜索“買不到碘片”返回條數是前一天的8倍。3月16日,大家開始表達“碘片買不到”,改為搜索“買碘鹽”。當記者在做一個報道訴求的時候,還是要一點一點改變社會。
總結起來,大數據時代,報道生產流程需要深度整合。而大數據時代會對深度報道帶來三個要求:精準、精確、精巧。對于記者來講,既要有理科的思維,同時又要有深刻的人文關懷。
張志安:
大數據對報道的意義是有局限的
10月1日天安門升旗儀式結束后,11萬人留下5噸垃圾。香港《文匯報》以此做了報道《愛國從不扔垃圾開始》。報道采訪了環衛工人和環衛部門,得到了這些數據,也做出了自己的角度。
但這個新聞發表之后馬上有人發了一條消息,講“11萬人5噸垃圾背后的故事”。一是天安門廣場為了安全不設垃圾筒。二是很多人前一天晚上11點就來熬夜排隊了。三是指出在香港維多利亞港搞狂歡的時候會產生20噸垃圾,在紐約或者倫敦的狂歡節也會產生垃圾。也就是指責記者沒有做數據對比,簡單把垃圾問題歸結為公民素質是不合理的。
10月2日,《新聞晨報》又提供了一個數字,說10月1日這一天的垃圾與十年前對比有所減少,所以說國人素質進步了。
我把這些文章放到我的客座總編微信群里討論,有一個總編說,那天下雨了,垃圾會增重,所以5噸垃圾可能實際只有3噸。后來馬上有人說了,11萬人5噸垃圾,重要的不是垃圾總量,而是應該比較人均垃圾,這才更有意義。
在日常報道中,其實記者經常涉及數據。但問題是如果記者不掌握一些必要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那么對統計的理解就非常單一。深度報道記者都知道,講出事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幫助受眾理解事實。在廣場扔垃圾,到底是結構決定行動者,還是行動者影響結構。所有的深度報道也都包含這個問題。大部分常態情況下,是社會結構決定你的行動。但是在特殊情境下,恰恰是你的一個反常行為改變了結構。
最后說一點,很多人一聽到大數據就容易神化這個概念,覺得大數據時代一切都改變了。其實大數據對深度報道有意義,但這個意義是有局限的。
陳芳:
在不斷變化的中國,新聞人應堅守什么
當代中國大家最關注的莫過于一個“變”字。中國的變化之大、范圍之廣、影響之深遠是世所罕見。在這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新聞人應該堅守什么?
新華社“新華視點”欄目誕生于2000年4月,至今已推出6000多條深度報道。現已開設的子欄目包括“新華視點觀點面對面”“新華視點交鋒”等。同時,從純文字向多媒體拓展,黑龍江衛視落地了“新華視點”的電視品牌。
“新華視點”主要聚焦三點:中央工作的重點,群眾關心的熱點,實際工作的難點。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延伸為五個提高:第一,深度調查提高競爭力。第二,輿論監督提高影響力。第三,熱點引導提高公信力。第四,通過權威解讀提高引導力。第五,展示人文關懷提高報道的感染力。時代在變,新聞也在變。但是有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在新聞面前記者無權回避,在真相面前人民有權知道。透明度決定著公信力,傳播力決定著影響力,話語權決定著主動權。
羅昌平:
微博時代對深度報道的影響
微博時代,碎片化閱讀的特點對深度報道產生了多方面影響。第一,記者的分裂感。我非常明顯地感覺到,最近幾年記者越來越難做深度報道。從捕捉到有價值的網絡信息到派人操作,有時需要兩個月,有時需要十天、一周左右。往往還要有好幾個記者配合、合作。可是等我們操作出來以后,這件事已經冷卻了。第二,報道的同質化。有時,關于一個主題的報道很難有不同角度。雖然在微博里可以呈現各個層面的聲音,在報道上卻難有高質量的突破。第三,公眾的淺閱讀。大家更愿意看140字能夠說清楚的東西,他不愿意再看一萬字的長文章。所以,《財經》雜志現在順應形勢。只有特別重大的題材才會花大篇幅去做。
現在記者的報道就像被置于四面都有觀眾的舞臺上,被全方位地展現在觀眾面前,只要有漏洞就一定會被觀眾發現。在此背景下,我提出了法經新聞學的概念。留意最新的諾貝爾獎得主,不難發現實際上很少再有一個人獲得某一項大獎,很可能是跨部門、跨學科的兩個人一起獲得的。網絡時代,打造全能記者是不現實的,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通力合作。我提出的法經新聞學跨好幾個學科,最核心的是經濟學和法學。中國現在的企業數據管理已經非常先進了,跟很多外企是一致的,所以可加大基于公開數據的深度分析報道。今年,《財經》雜志增加了法經刊。由于趕上了紙媒整體下滑的軌道,成本急劇上升。我們采取重頭報道自采,其他稿件約請專業人士撰稿。
王星:
幾招實用的搜索小竅門
巧用信息公開條例。在美國大使館發布的空氣污染指數受到網民關注的時候,《南方都市報》向全國31個省市區的環保廳同時遞交了PM2.5數據信息公開的申請。歷時一個月,最后收到10個省市區的回復,最終做出了一組探討性稿件。后來,我發現信息公開條例對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是壓力。有時記者援引條例去采訪地方政府相關負責人,得到回復的速度比聯系其宣傳部門還快。
巧設搜索關鍵詞。《南方都市報》深度部2006年創刊“網眼”板塊,我是第一任編輯,做網絡方面的探索比較早,有些經驗可分享。
操作轟動一時的昆明因上馬化工廠而實名制銷售口罩的新聞時,我負責提供后方支持。怎樣從網上找到有用的線索?在中石化項目宣布上馬之后,和媒體報道昆明實名制銷售口罩之前,這個時間段里有沒有人探討過口罩?如果有,那么就很有可能是記者需要的信息。
我搜索到了很多類似于這樣的信息:“今天上午工作人員到店通知:購買口罩需要實名制”。這個信息是很重要的線索,但是記者據此采訪相關部門的話他們不承認,記者也無法拿到他們的文件。其實接下來可以這樣設定搜索關鍵詞:口罩 實名制site:.gov.cn,立刻就在昆明工商紅盾信息網上發現了一條消息:“迎南博、保穩定,呈貢工商在行動”,在這里口罩銷售實名制被當作工作經驗進行交流。
順著這條線索,記者可以進一步瀏覽當地各個工商局的網站,會發現更多相關線索。記者瀏覽信息時會發現很多網頁提及“迎南博”。那么可以再用“迎南博”作關鍵詞搜索。這樣線索越來越多,而且都是非常權威的,無法被顛覆的線索。
北京市南三環某地曾發生過一位名叫袁利亞的年輕女子墜樓事件,這事很快發酵成熱點新聞。想做深度報道,首選當然是一線采訪。但在后方可以做什么?搜索“袁利亞”,鋪天蓋地的是有關她在京溫大廈自殺的同質化新聞。但是搜索“袁利亞 —自殺 —京溫”,就可以屏蔽掉“自殺”和“京溫”兩個關鍵詞,于是順利找到她的騰訊微博。如果你是第一個找到她騰訊微博的記者,或許你就能成就一條獨家。
張寒:
網絡時代,深度報道的輕逸與沉重
在我看來深度報道是傳統媒體最具專業水準的報道形式,在網絡時代,它既要維持之前的沉著與厚重,也要有網絡時代的輕逸。
首先,重大突發,解放單兵。在重大突發中,記者到現場往往會因為信息缺失在幾個現場間疲于奔命。我們現在的解決方案是后方依靠網絡和電話采訪找到關鍵點,記者單兵突進。操作2013年上半年的廈門縱火案報道時,前方記者趕到時已是中午。我們安排他直接去找縱火者陳水總,在幾小時之內操作出了一篇不錯的人物報道。后方則統籌了占據近兩個版的《47人的生命終點站》,通過三個記者對目擊者的采訪完成對爆炸現場的還原;另一篇《廈門BRT公交車安全五問》也是后方記者通過電話連線完成的。
其次,壟斷式追蹤。持續不斷的追蹤成為網絡時代的致命武器。在我們看來連續性的追蹤也會不斷深入。
再次,網絡時代如何守住獨家。微博進入公眾場,獨家越來越難,正因為難得,所以更加珍貴。《新京報》王林報道是我操作的。我去王林家的那一周,每天思考的就是怎么既要把稿子的基礎打牢,又要守住獨家。我每天早上起床最恐懼的事情就是上網搜索看有沒有人發稿。不過,我發現守住獨家后就非常容易了,后面的料可以慢慢放出來。而且,報道反響很大,我基本上每天都會從呼叫中心接到電話說有人爆王林的料,料的來源也非常清晰,操作起來很常規,效果也很好。
最后,輕盈的趣味。網絡時代,有趣顯得無比重要。意義當然重要,但有時候有讀者看到一個有趣的新聞,他覺得已經足夠了。他只是需要這一點。這也是深度報道在未來需要探索的。此外,形式的趣味性《新京報》也在探索。我們現在也在嘗試數字化的表達。當文字的表達很難往前進一步的時候,我們也會發現圖表的力量。
現在,有的記者專門承擔不停息的追蹤職能。我們希望網絡時代有記者有更多時間可以追蹤報道。網路時代同樣應相信緩慢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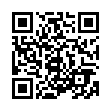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